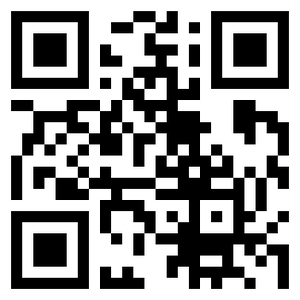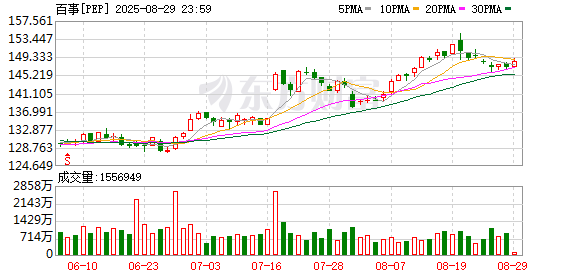《游牧的人类学家:巴特的人类学旅途》
作者:[挪威]埃里克森
译者:马建福
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5年5月
避免将社会生活简化为表格和数字
巴特在纳菲尔德讲座的演讲非常精彩。在场的一名学生,现在是一名经验丰富的社会人类学教授,回忆道:巴特站在讲台上,个子高高的,浓密的黑发在灯光下从他的头上流下来,使它看起来像一个光环。
展开剩余87%研究员巴特。图片经戈斯塔·哈玛隆德许可使用。《游牧的人类学家:巴特的人类学旅途》插图
《社会组织模型》(后简称《模型》)可能是巴特人类学视野中最重要、最广为人知、可能也是最容易被误解的著作。《模型》基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1963年的讲座,于1966年初出版。从外观上看,它并不是一本特别引人注目的出版物。这本小册子包裹在一个略带灰色的绿色纸板封面里,只有32页大开本密排的内页。
20世纪80年代初,当我在奥斯陆学习时,一年级社会学学生需要阅读整本小册子,而社会人类学学生只需要读第一章,关于交易的那一章。这是我作为社会学学生阅读的首批文献之一,对我们这些已经习惯于阅读大多简单、近乎口语化的课程材料的学生来说,遇到巴特这样的枯燥、简洁的写作风格,不能不感到震惊。从那份文献中若想得到什么,除了苦读,别无他法。从一开始,读者就必须想办法来消化其浓缩的表述,例如,“根据一套规则(印象管理的要求),从更简单的权利(状态)规范中可以产生复杂和全面的行为(角色)方式的模型”。甚至渔船上的简单关系也是以一种简洁的、技术性的风格描述的,这样就难以形象化地呈现渔民、船长和网头。五年前出版的关于巴赛里的书更引人入胜。但是《模型》是他最雄心勃勃的理论文本,看起来巴特在撰写时似乎力求字字珠玑。在这方面,他无疑取得了成功,但结果却是学生们不得不像用锤子和凿子一样对付它。
在《模型》中,读者会发现一种尝试:即将社会研究科学化,其前提是避免将社会生活简化为表格和数字。每个认真阅读这本小册子的人都明白,他们是在面对一个思想家,他同时又是严格归纳的——他没有提出任何缺少经验发现支持的主张——和概括的。他在寻找普遍的机制和一些简单但有效的模型,以便能够对社会形式做比较。对此理论模型的一个普遍反映是抱怨交易概念过于突出,把人变成了类似于商学院经济学家之类的东西。因此,许多读者(包括我自己)花了很长时间才理解生成过程分析的含义,在这种分析中,被预见的是社会生活的动态本身,而不是凝固的形式;而社会形式只是在持续不断发展、目标导向的互动中暂时得以维持。
有史以来听众最多的一次演讲
在巴特之前的许多社会科学家都强调策略选择和利益最大化。功利主义这个术语经常被用来描述他们的工作,通常是以一种贬低的方式。巴特最初的贡献主要在生成方面,这是一个前提,即个体策略(a)是在如此多样的环境下采用的,以至于人们几乎必须是人类学家才能理解它,他们(b)在不同的条件下创造不同的社会形式,以及(c)研究的中心任务必须包括解释这种变化。
巴特的模型之后受到广泛的批评,但批评的要点在几年之后才得到发表。首先必须阅读和消化这本小册子。随着历史似乎在1968年向左急转,这些批评就带有政治紧迫性的色彩,这在1963年讲课时或1966年发表时是没有被预料到的。仅就当下而言,《模型》只是作为巴特对人类学理论最有原则、最彻底和最有计划的贡献而存在。
《我们的起源》(2011)剧照。
除了纳菲尔德讲座之外,另一个重要的邀请是在1966年秋季的美国人类学协会(AAA)会议上就社会变迁问题做一次主题演讲,另一位演讲者是马克斯·格卢克曼。两位学者都曾研究变迁过程。格卢克曼是拉德克利夫布朗的直系学术继承人,他通过关注具体社会的动态,把自己从一些结构功能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他仍然假定存在促进整合的社会动力。巴特更进一步,他倾向于认为社会是一个相当不稳定的实体,总是在形成中。他有时把社会简单地称为策略行动的“综合效应”。据说,格卢克曼在讲座开始之前极度紧张,感觉到他的演讲永远无法与他这位年轻同事那颇具魅力的权威相匹敌。
这将是巴特有史以来听众最多的一次演讲,有几千名听众。标题是“关于社会变化的研究”,和前一年的纳菲尔德演讲一样,它原本就是按部就班的。然而,其方法和主题不同。虽然纳菲尔德讲座与《模型》的第一章有很多共同之处,但美国人类学协会讲座与第二章的主题相同,即与连续性、整合性和变迁有关的问题。巴特在这里主要使用达尔富尔的例子,社会系统的稳定至少和它们的变化或不稳定一样令人困惑。他谈到创业带来的变化和个体之间新机会的发现,这往往是环境变化的结果,但他也谈到稳定的机会条件带来的连续性。其他人可能会强调习惯的力量、对安全的需求或既定社会制度固有的惰性和弹性。但是这些都不是弗雷德里克·巴特的观点,他是一个不寻常的人,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这得益于他自己与世界的接触体验。
《族群与边界》是被引用最多的人类学文献之一
20世纪60年代中期是巴特职业生涯中最繁忙的时期。他在国内外写作和演讲。在伦敦和美国人类学协会的讲座是最重要的,但他也去了其他地方,并且让卑尔根的交流活动继续下去。1964年,他为弗斯和经济学家巴兹尔·亚梅编辑的一本书撰写了一章关于巴赛里人经济的内容,同年,他撰写了一篇关于巴塞恩人和俾路支人领地边界的民族过程的文章,发表在乔治·莫根斯蒂纳纪念文集里。他还为区域民族志的丹麦读者写了另外两篇关于巴赛里人的文章和一篇关于中东的长篇文章。尽管在苏丹待了一年,但这期间他不再从事田野工作。与此同时,这些忙碌的岁月似乎只带来了成功。这无疑增强了他的信心,但他也发现了一些其他忙碌的人可能会认同的道理,即做很多事情的人总是会找到做更多事情所需的能量——只要他们能在正在做的事情上取得成功。后来,这种现象通过心流心理学得到描述。巴特本人这样描述20世纪60年代中期:
那是一个非常丰富多彩、鼓舞人心和富有挑战的时期,发生的许多事情也许可以说让我有点虚荣和自负,因为事情进展得非常快,每次都有成功的可能,我似乎每次都会成功——无论是在研究地、在皇家学会、在美国人类学协会、在社会科学学院的部门和委员会。似乎没有什么能够限制一个人的成就。
那是一个非常丰富多彩、鼓舞人心和富有挑战的时期,发生的许多事情也许可以说让我有点虚荣和自负,因为事情进展得非常快,每次都有成功的可能,我似乎每次都会成功——无论是在研究地、在皇家学会、在美国人类学协会、在社会科学学院的部门和委员会。似乎没有什么能够限制一个人的成就。
对巴特来说,他的野心随着成功越来越大。关于他专注和高效的故事达到了神话般的程度,但事实是,他认为自己基本上是一个相当悠闲、几乎懒惰的人。他必须给自己设定最后期限和目标,并强迫自己去实现它们,这一方面似乎颇为有效。另一方面,如果巴特在20世纪60年代大量的写作和演讲展现了他巨大而持久的能量爆发,那么他在卑尔根的同事们的生产力就明显下降了。卡托·瓦德尔是一个例外,他发表甚多,但野心不大,最终只发表了挪威语文章。社会学家欧文·汉森曾做渔业项目研究,从未提交一份完成的出版物。布隆没有发表多少文章,但发表了几篇文章,其中一篇是社会语言学的经典文章。后来,约翰·甘珀兹、哈兰、西弗特斯、格伦豪格和亨里克森都将发表专著和文章,但无人像巴特那样雄心勃勃。在卑尔根的公共休息室和走廊里,人们有时会说,尤其是回想起来,大家写东西只是为了放在抽屉里,因为他们害怕弗雷德里克会对他们的业绩说些什么。很难判断这究竟是借口还是解释,答案可能是两者兼而有之。
虽然巴特没能把他的同事变成多产的作家,但至少确保他们做了田野调查。在20世纪60年代,哈兰去了苏丹,西弗特斯去了墨西哥和秘鲁,布隆去了挪威和巴哈马的山谷,格伦豪格去了土耳其和阿富汗,瓦德尔去了纽芬兰,亨里克森去了加拿大的纳斯卡皮(因努),扬瓦尔·拉姆斯塔德去了美拉尼西亚,贡纳尔·索博在苏丹做了田野调查,齐格鲁德·贝伦岑几年后在卑尔根的一所幼儿园也做了同样的工作,而努尔夫·古尔布伦森去了博茨瓦纳,他们在方法和理论上都受过良好的训练,甚至在五六年的时间里,巴特成功地在一所周边的小型大学里建立了一个充满活力的人类学社区,这被许多人所羡慕。
巴特只有三十多岁,但他已经在人类学领域活跃了十五年了,他已经确立了自己作为一个重要人物的地位。因此,1967年初,当他向温纳格伦基金会申请资金,组织一个有十几个斯堪的纳维亚同事参加的关于族群关系的研讨会时,申请立即获得批准。事实上,他还被鼓励提出申请。这次研讨会成果最终汇编成册,成为至今仍是世界上被引用最多的人类学文献之一,即《族群与边界》。
本文选自《游牧的人类学家:巴特的人类学旅途》,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文作者/[挪威]埃里克森
摘编/何也
编辑/张进
导语校对/赵琳上海股票配资平台
发布于:北京市中融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